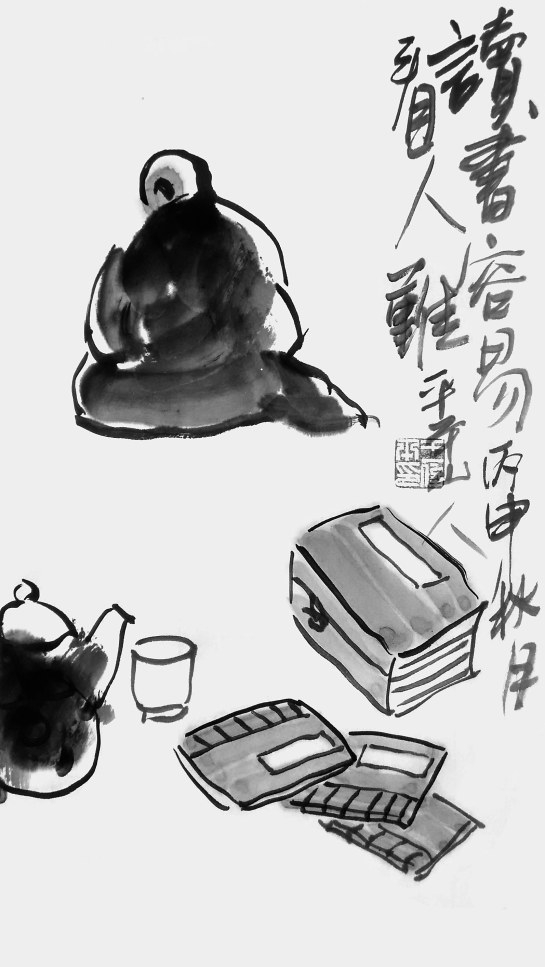
□张林 他们的外号,有故事的外号,却如一粒粒种子,在人们的心田里扎下了根。 身边有些人,即便很熟悉,也有叫不出名字的。不是他们没名字,只因习惯了叫他们的外号,实际的姓名也就给忽略了。 其实,名字只是一个符号,叫出与否,没什么关系,也没那么重要。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是:他是否深刻地留在了别人的记忆里。 小时候,我生活的屯子里有个半大小子,他是孩子王,他姓百,大人们都叫他老百孩子,我们这些跟屁虫也跟着叫他老百孩子。 记得那是一个哑巴冷的黄昏,我们一群孩子,正在南大坑那如镜的冰面上抽冰尜,老百孩子走上近前。也许我手中的皮鞭子对他有了什么启发,他向我扔了一句:“我用用你的鞭子!”未等我做出任何反应,他便很霸道地夺鞭在手。他是孩子王,屯子里的孩子见到他都心生惧意。我自然大气不敢出,随着他奔向生产队的院里。 生产队的谷草棚子旁边,聚了好多人,不知出了什么事。我好奇地凑上前,谷草棚子里蜷缩着一个蓬头垢面的人。只见老百孩子挥舞着鞭子,一边训斥蓬头垢面的人“你个狗特务”,一边恶狠狠地向他抽打。 当时,我恨不得自己立即长大,愤然冲过去,从老百孩子手里夺回我的鞭子。我觉得老百孩子如同电影里的汉奸,不是什么好人。 也许老百孩子打够了,玩够了,他转身把鞭子还给了我。望着他一脸得意,我突然觉得这个孩子王是恶魔王! 我攥紧鞭子含泪跑回了家。望着心爱的鞭子,原本油黑的皮条已成了黑红色,我放在清水里洗,可无论怎么洗,也感觉洗不掉那黑红色。心爱的鞭子,也仿佛幻化为一条长信的毒蛇。最后,我赌气把鞭子填进了火苗正旺的灶坑里。 也因为此,老百孩子这个不像人名的名字,便刻进了我的记忆里。 读小学三年级时,我的班主任姓贾,大名叫什么,我们真不知道,就是现在也不知道,学校的老师都叫他贾祥子,我们当着他的面叫他贾老师,背地里都叫他“假如”。 当时,贾老师对我们绝对很严,更有成绩要求。记得一次,他出一套数学题考我们。公布成绩前,站在讲台上的贾老师面沉似水。我们都伸长脖颈,屏住呼吸。突然一枚大号洋钉好像变魔术似的出现在他的手里。只见他手持这枚大号洋钉,扯开大步,走下讲台。全班40多名学生,他居然挨个敲打男生女生的头,只有我例外,因为我及格了,我考了61分! 贾老师除了教我们数学,还兼我们地理课。他的外号,也是因为他上地理课有个口头禅。 地球人都知道,地理学科,老师不重视,学生也不重视。可能贾老师也不太认真备课,他讲的时间短,划题的时间长。勉强讲一点儿,贾老师也不去考虑语言的什么连贯性了,信口开河,东一句西一句,经常是张口假如闭口假如,比如说:“假如呢,假如我们家乡的地理状况呢……”时间一长,我们全班学生也都“假如”起来。回家当笑话说,家长们也跟着我们“假如”了。 上个世纪80年代,在文化乡教学那些年,我家后院的邻居,总求我为她代写书信。那个年代没有现如今的便利通讯,手写书信是与外地亲人朋友联系的主要工具。 这位比我年长十几岁的妇女,其丈夫排行老三,见面我叫她三嫂,通常情况叫她“三老跑”,她自己也很习惯大伙叫她“三老跑”。“三老跑”这个外号,是身边人赐予她的。怎么回事呢,她婚嫁本地后,大伙就发现她走路从来都是带着小跑,她性格也属于风风火火的那种,因此就有人给起了这个外号“三老跑”。 她本人也十分认可这个外号。每次为她代完笔,我问她信的落款怎么写,她说别写她的大名了,大名谁都不知道,就写“三老跑”吧。我有心问她真名叫啥,她说告诉你没啥用,告诉你也记不住。 有一天,一位亲属给母亲过80大寿,非坚持让我给写礼账。因为身边人,我大都知道外号而不很清楚他们的大名,我极力拒绝,可最后还是拒绝无效,硬着头皮答应了。 一位开饭店的老板娘去随礼,我问写谁的名字,她笑了,不写我,也不写我家那“死鬼”。我笑了:“那写谁呀?”“你就写‘骨头王’,谁都知道。”她说。 “骨头王”?可不咋的,一说“骨头王”,几乎全镇人都知道说的是他们两口子。“骨头王”那可是他们两口子的饭店最叫得响的招牌。 身边的这些熟人中,有许多人的真实名字,都随着岁月的老去,而淡出了人们的记忆。他们的外号,有故事的外号,却如一粒粒种子,在人们的心田里扎下了根。他们就像那些不知名的花草,即便叫不出真实名字,也不会影响生长。但如果给这些花草起个有趣的外号作为名字,多么明了,多么生动,多么令人难忘啊!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已故多年的外婆的名字。外婆那多如繁星的“瞎话”,是我最早的文学启蒙。我从心里想知道外婆的名字的时候,外婆已不在了,当她将自己的一切还给泥土,也带走了她的名字。 王俊平《读书容易看人难》 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