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地漠北的诗意书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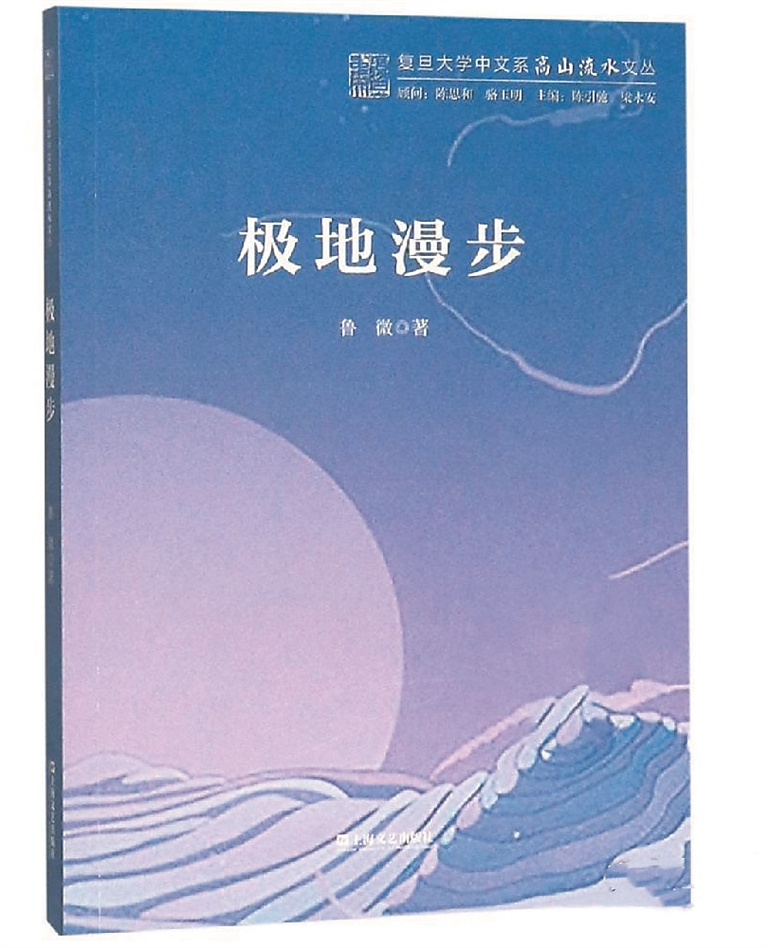
《极地漫步》 复旦大学中文系高山流水文丛 鲁微 上海文艺出版社
□聂茂 李馨然
鲁微是我在鲁迅文学院和复旦大学作家班的同学,多年来,他坚守在大兴安岭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置身于沸腾的生活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现场,认真观察、思考和书写。《极地漫步》是鲁微的最新诗集,也是复旦大学作家班30周年的献礼之作。这部诗集从自然地理、风土人情、历史见证、生命沉思等多方面展现了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的历史变迁,诗人以热情洋溢的主观情志为“诗血”,在大兴安岭自然原态的美与真、历史变迁的厚与沉的诗歌主题下,嵌入的是自我关于“开发一代”先辈生命历程的记录与铭刻,以及对于北国极地人类本原存在生命的追问与沉思。
松脂味道的深刻记忆:
大兴安岭大开发的鲜活书写
在大兴安岭这片曾经贫瘠寥落的土地上,发生过太多惊天动地的故事,也留下了太多中华民族缓慢成长的艰辛印记。循着诗人鲁微或清浅或深刻的文字缓缓回望,70年漫长开发历程也充满了淡淡的松脂味道。在《察哈彦的天空》里,诗人用生动形象的笔触描绘了“八万知青逆水而上”,用自己的辛劳和汗水开垦新麦田的宏阔场景。由于为这片土地付出了太多,他们早已将此处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即使奋斗的汗水与思乡的泪水一起流干,“万千知青的双眼”却依然饱含深情地注视着察哈彦,其依恋之情如青烟般淡淡萦绕在“察哈彦对面的陡峭山崖上”。
大兴安岭的三合村,像二战前的诺曼底一样默默无闻,直到“不计其数的开发大军”,和“胸怀大志的知识青年”在此登陆。在开发人员的努力下,“条条公路通达星罗棋布的林场”,“长长的铁路贯通横断大山”,“一座座林城拔地而起”,“一列列木材运赴祖国内地”(《父辈的三合》)。正如他在《猎手》一诗中所写:“真正的猎手,不需要声音,任何的声响,哪怕是一束阳光的泻落,也会让整座森林感到惊慌。”三合的崛起正是如此,悄无声息,却直击要害,一代人的血汗浇灌着它,而它也迈着日益矫健的步伐向先进文明突击,并将关于大开发的鲜活记忆深深刻入中华民族奋发图强、自强不息的历史中。
开荒建设者的心灵史:
大兴安岭不凡征程的诗意记录
对个体而言,70年很短,不过是凡人的须臾一生;可是对一个地区而言,70年却漫长到可以完成从“北大荒”到“北大仓”的巨大飞跃。黑龙江的大兴安岭有一个地方名为卡伦,它是一个“小得会被所有人遗忘”,甚至事实上也被“遗弃百年”的无主之地。但是卡伦尽管“独自沧桑”却“总不悲伤”,因为有“鸢尾花、败叶草、白桦树、小溪流”(《极地卡伦》)等伙伴一直与它相依相偎、不离不弃。虽然“我”刚“到达小镇”的时候也曾感到“一阵眩晕”,“似乎忘记了我是谁,我在哪里”,可是相处久了,“我”却被它的天然之美所深深震撼,它已经成为了“我最美的家园”,与我难舍难分。通过描绘卡伦的寂寞境遇,以及“我”看待它的前后心态之不同,诗人将知青们在建设这片土地的时候慢慢发现它的美并逐渐爱上了它的心灵活动刻画得惟妙惟肖,“我”的转变史代表着一代极地北疆建设者的心灵史,呈现出宏大而磅礴的诗意。
诗人的朋友被分配到严寒的漠北工作,却从未有过不满和抱怨,而是用兢兢业业、披肝沥胆的任劳任怨,带领漠北的旅游业繁荣发展。“零伤亡、零灾害、零事件”是他的赫赫战功,可克俭奉公的他“却从没领过哪怕最小最小的一枚奖章”。一个对土地和人民充满爱意却从不居功的建设者形象如在眼前,让人情不自禁生发出由衷的敬佩之意。
聆听极地之侧的心跳:
关于自然与人类生命的沉思
“真正的北部,在北方以北”,这是极地之侧,是容易被人遗忘却又充满生机的地方。大兴安岭的一年只有两季,度日如年的冬和转瞬即逝的夏。可尽管“时刻都在与寒冷对峙”,北部却“从不找任何借口而丧失自己”,用傲然挺立的“骨气”将自己塑造得“浑圆而笔直”,展现出强大的自然生命力。大兴安岭的环境究竟有多恶劣?诗人用《大兴安岭:一只清脆的风铃》《大兴安岭:一匹执著猎马》《大兴安岭:杜鹃满山》三首组诗为我们刻画出一幅真实的荒凉图景。在大兴安岭,唯有沉默的森林肩负着抵御西伯利亚寒流的使命,它兀自对抗起风雪,大兴安岭是三江的源头,滋润、护佑着三江平原的万顷良田。寂静无声的它是美丽而孤独的,即使“心被刺痛、歌声带血”,却依然坚持发出“清脆声声”。大兴安岭的严冬如此漫长,望眼欲穿地等待却连“哪怕一个字的春的序言”都迟迟未到,夏天就在不经意间突然到来,将满山的红杜鹃都羞煞了。
在一年有8个月都被霜雪覆盖的大兴安岭,生命要如何顽强、乐观和积极向上才能存活下来呢?在《坚硬的树木》一诗中,作者揭秘了森林里所有的叶子,都只能以最迅捷的姿态迎接简短夏日里仅有的那一点水的真相。由于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所以树木们“总是目睹自己的叶子早早被渴死”,也正因为这样,最后存留下来的树木,“从里到外,都坚硬无比”。
作为普通人的我们,要如何学会对抗庸常、享受生命呢?或许,我们所真正需要的,也不过是简单的四个字——把握当下而已。人类的生命代代无穷已,过于追求宏大的完美无异于蚍蜉撼树,生活在此时此刻,或许便很好。心浮气躁时,不妨静静观赏屋后那“一条一直以来默默流淌的河”,它曾见证过“异国的少女唱歌、起舞或濯衣”,也以温柔的方式聆听过“大地的心跳”和“生命的声音”(《屋后的河》)。“它的名字叫黑龙江”,它只是一句话也不说地静静流淌着,却比一切喧嚣都更加懂得生命的真谛。由自然之生命而及人类之生命,而人类从自然中来,最后也不可避免地要回归自然,因此向大自然学习不可谓不是一种智慧,是值得我们人类穷尽一生也要探索的真理。
极地漠北的缩影:
历史的哨音与文明的变迁
寂寞的北地在无人问津之前,也曾有过繁华沉重的历史。在十八驿站,“康熙年间的气息仍在弥漫”,它曾见证过“四百多年前的馆驿里多少的爱恋”(《在十八驿》)。300多年前一个弥漫着浓雾的正午,名为萨布素的将军在漠北展开了一场收回失地的战斗,“战马嘶鸣、夹杂着涛声,两军对垒、生死于一瞬”(《雾中雅克萨》)。这片故土曾经有多少英雄踏过,今日就将有多少建设者前仆后继,顽强拼搏、永不放弃的精神在延续。诗人在城市里的每日每夜,都会“依稀记起森林”,“记起灵芝和年轮扩散的痕迹”(《城市:每日每夜》),从历史的角度观山海变迁,这钢筋水泥织就的小屋,之前也不过是覆盖着石头的洞穴、大海或森林。物换星移、沧海桑田,在鲁微笔下,于极地北疆的角色变迁中,生命与历史交缠成诗意的风景,等待着你我的驻足与聆听。
任何鲜活的历史都是当事人的心灵史,由自然地理入风土人情,从历史见证联想到生命沉思,鲁微迈出了用诗歌书写大兴安岭地理历史的一大步,也是其创作生涯突破的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