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穿越,但永不能抵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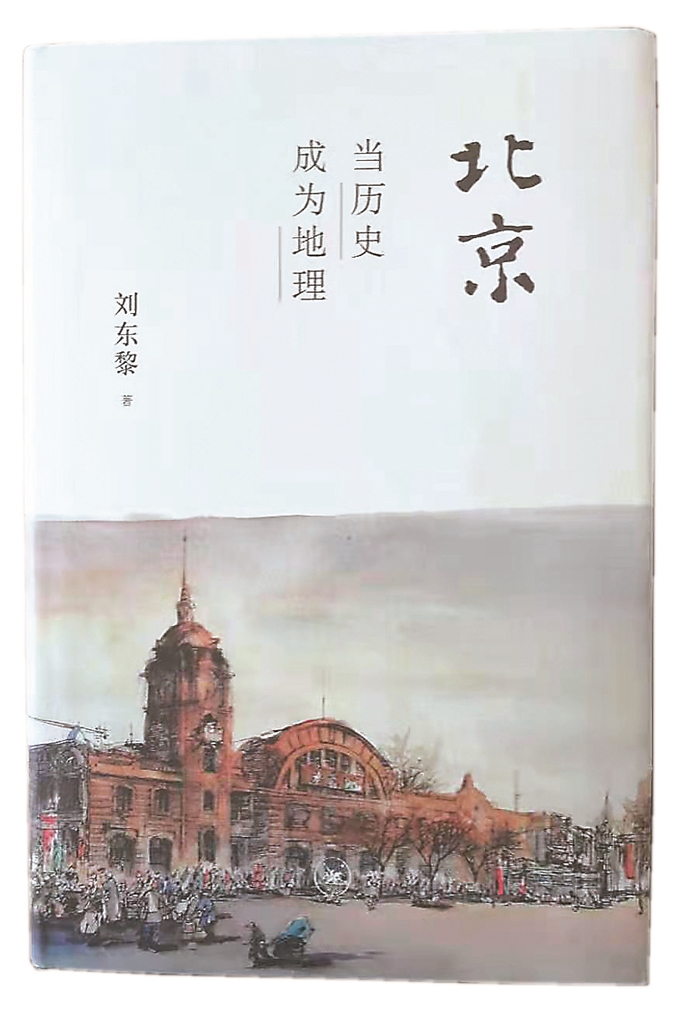
《北京 当历史成为地理》 刘东黎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3
□刘东黎
世间万物从一个梦开始。那是模糊不清的事实、神秘的事物、真实的历史与想象混合在一起的谜团。对我而言,北京就是这样一座梦之城。很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写一系列关于北京的文章,想要深入到这个城市的历史深处,找寻一座古城恒久的价值和情感。
为着这样一个理想,我日复一日地穿行在这座城市里,流连在北京的历史遗迹或旧址之间,有心无心地走过胡同、茶馆、庙会、图书馆等旧北京所特有的公共场所。时间久了,会有一些难以言说的感受,这些感受从那些建筑或它们残留的遗迹里,从它们周边的每一寸空间里,渗透出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北京城正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怀乡病候的一个重要根源。那些充满离合之情、兴亡之感的历史章节,令人时而激昂,时而沉默,时而旷达,时而忧郁;在波诡云谲、起伏跌宕的沧海桑田中,那一幕幕惊心动魂的场面,那一幅幅光照百世的剪影,那一个个令人低回的细节……无不是带着灼热的碰撞、融汇、涌流、喧嚣、奔腾,贯穿着一个城市的古老经络和文明的汩汩血脉,使其定格为永恒的一瞬。
我发现,我身边的很多人,虽然身处北京这座有着无尽宝藏的记忆之城,却极少产生过要了解它的愿望。虽然随便去找个公交车站牌,都能找到长城、故宫或者颐和园这样的大名;而雍和宫、白塔寺、钟鼓楼……几乎只是上班途中匆匆路过的一个地名。北京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一个单向度的线条,我们已经没有愿望去展开它的细节。
这种失之交臂是多么让人惋惜。我们都差点忘记了,北京是世界上规模最为宏大的古城,它最完美地保留了中国古代城市结构;宫殿、坛庙、街巷、府第、花园、商区、河脉、桥涵……大都准确地停留在原来的位置上,历经朝代的更迭或者全球化的冲洗,它的筋骨血脉都没有变形;从整个古城的格局,以及散布在全城的文物建筑群来看,它完全就是一个没有屋顶的封建社会历史陈列馆。它神秘、幽远而又宏大,足供我们探查和寻访。一个这样的城市,是能够让人肃然起敬和流连忘返的。
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历史与地理交融的北京——那个隐藏于时空变迁下的北京。
对于我来说,关于北京的行走,不仅仅是脚步的,更是思想和精神的。一幢老的建筑,或许就能让我接收到一种生命透过高墙而发出的信息;残砖断瓦与衰草连天的萧瑟,会给予我一种无以名之的年代感。若是有了不经意的怆然感触,为遥远年代的人或事牵动心魂,一个人就会在生命信号的这端,无形中接上了祖先高古的气脉。正因如此,我注视北京的目光里,更多了一抹遥远、深阔和缤纷的色彩。
早在1901年,梁启超就在《中国史叙论》里指出:“地理与历史,最有紧切之关系,是读史者所最当留意也。高原适于牧业,平原适于农业,海滨河渠适于商业。寒带之民,擅长战争;温带之民,能生文明。凡此皆地理历史之公例也。”
是的,世界上任何一处经度和纬度的交点,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再美的风景,也不是孤岛上一座昨天才刚刚建起的花园。时光流转,大地上的一切并没有随风而逝,历史和地理给予时间和空间的交错,从而构建出一个城市的内核,融合在地理之中,亦无法剥离出历史之外。
而北京这一方水甘土厚、风高气寒之地,在从前无人知道的某一时刻起,就点燃了最早的火光,整个华夏的历史,都在周口店深山里的那丛火光的照耀下开始熠亮。春秋战国时代,北京就是燕国国都,辽置陪都于此,金正式建都,公元1421年,大明王朝的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从此改变了中国地缘政治的格局,奠定了北京在政治版图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以后的六百年间,北京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太大了,历史太漫长了,她有着过分良好的胃口,那些别的城市无法应对的挑战和苦难,北京似乎坦然地就消化掉了,这座业已存在了三千年的古老城市,拥有着一种沉稳的力量、雄浑的元气以及俯仰人间世界的天地血脉。在所有的表象之上,北京可以面对世事的任何变迁。这些足以让我们体会到,古城北京的生命力是怎样地顽强。
历史是地理的第四维度,它赋予地理学时间与意义——房龙曾经这样说。北京有着世界城市建筑中历史文物建筑最多的绝世孤本,富有历史的质感和文化的多样性,像一条无比丰富的文化图链,凝聚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和时代特征。它承担的东西太多了,不仅仅是现实本身,还有历史的、哲学的,以及某种象征意义上的。历史在递嬗过程中并非一切都是从头开始的,比如说,古老的建筑就是我们与古老文明之间的一个绳结。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仿佛读懂了世界的暗示与隐喻:我们只是古典文化遗产的暂时托管者;我们并没有权利对它们进行无所忌惮的铲除和损毁。
北京的城市改造日新月异,我们也期待着一个更文明、更理性、更开阔的北京,以一种优雅的姿态,从容走进国际社区。个性张扬的西方现代建筑,密布的交通网路,完整的污水处理系统,进步的电子服务技术,与国际接轨的观光设施——我们满怀激情拥抱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这一“不容置疑的信仰”。只是我多么希望,这一信仰的代价,不是“花棚鱼池院落”、“胡同深处人家”这一高贵而优美的北京的彻底消失。
当我们静下心来,悉心打量这座城市,原有的一切,就会从时代多声部的喧哗中,慢慢浮现出来,如同一幅在斑驳的尘埃中逐渐显形的古画。它在表面上是拥挤的、疾速的,而本质上却是安静的、疏朗的、悠缓的;甚至是高雅的、精致的、深情的;那一份久违了的神定气闲的舒缓,正是这个城市的伟大之处。它像京剧,永远在那里悠扬婉转、不急不躁,水袖流转间,对所谓现代节奏置若罔闻,只有以从容的心对待它,才与它的美相配,才能于单调枯寂中,领略到满目的喧嚣,只是瞬息的繁华。
作为旧时帝都,北京不可避免地带有王者气象,它是权力的角斗场,同时又是新文化的发祥之地;它是悠闲的,同时又是趣味的。北京的现代形象,正在消磨掉其千年以来积淀的历史想象,以及蕴含其中的那份堂皇、平和、清雅。祖先前辈师长把遗产交到我们手上,我们却没法把诞生那份遗产的风物现场一并保留下来,当新一代的孩子们开始学会四下寻觅时,还能找到多少与之匹配的诗境和画境?当他们登临远目,抚今追昔时,又该如何化解由此引发的怆然寥落之情、无常幻灭之感?
我经常一个人怀想业已逝去的那个辉煌的北京城。长达四十公里的雄伟壮丽的北京城墙、无数座寺观庙宇、遍布京城精巧绝妙的牌楼……漫步在那样一个布满史迹的城市里,看是自然的漫游,观赏现实的景物,实际却是置身于一个丰满的有厚度的艺术和历史的世界;如同诵读着古人的诗书,你倾听的实际上是传统和文化的回音。我们欲使北京重生的愿望是如此之强,但我们是不是使错了力量,偏离了方向?我们以鲁莽的勇气洗刷掉了不少城市的灵韵,而那些东西曾经是如此的优雅精致。也许,那些事物对于我们来说,本就是太过于奢侈,以致于我们不配拥有?
变化是宇宙间的根本法则,世间万物无不处于永恒的运动和变化之中。生命在于运动,一切事物包括生命本身的意义都在运动中才能体现。我们不一定去寻找那个悠远宁静的北京,比如说那个多风沙、多国槐的,那个红墙绿树灰楼大院,大路宽广自行车汹涌的旧京。虽然我还是爱极了这份旧,怀旧的旧、返朴归真的旧,爱它的温和与沉静、质朴与抒情。然而新北京不仅意味着更多建筑的增加、更大面积的绿化、更便利的交通,它更意味着这座城市与她的人民可以拥有更为丰富的内心世界,它让我们在一座大城里生活而不感到孤单。文化总是在新与旧的张力中生存发展的,缺乏新的接续,文化不能延续,然而没有历史,也就无所谓了文化。一座好的城市应当像一条从历史潮流深处驶来的帆船,带着患有都市焦虑症候群的我们,轻快渡过时光的河流。
本书中山水、园林、城墙、胡同等形象,是把我们的思维引向遥远时间和空间的符号,既足赏心,亦寓警策。隔着那么多的神秘,隔着那么多遥远得叫人眩晕的岁月,我愿北京的文化气韵与历史记忆,穿越世事和政治的风雨,化为悠扬欣悦的市声和平静安闲的对话,在安宁和幽静的灯火阑珊处,变为我们心里最温情的底色。
(作者刘东黎,作家、文化学者,黑龙江籍。著有《北京的红尘旧梦》《月涌大江流》《印象玫瑰》《生若幽兰》《江河在上》《黄花落,黄花开》等多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