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那些教授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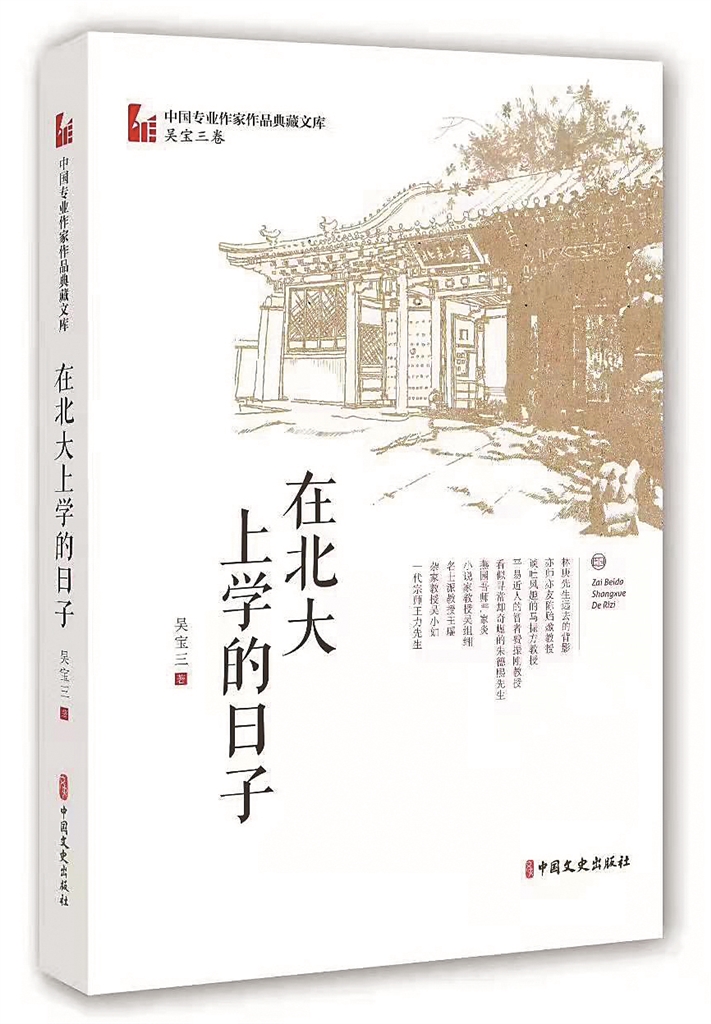
《在北大上学的日子》 吴宝三/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年1月
□嫩江渔樵
作者吴宝三是上个世纪特殊年代在北大读书的学子。他在书的自序中写道,“心系未名湖,情系未名湖。哪怕在梦中,我——一只北疆的飞雁,常常回到书声琅琅的湖边,栖息在她那温暖的臂弯里”。本书作者写了与北大中文系十一位一流教授在一起相处的日子。
林庚教授是对作者影响最深,也是作者置于篇首、单篇着墨最多的人物。
作者这样描述林先生的:“在那样革命的年代,衣着样式单一……而林先生穿着十分讲究,举手投足,一派地地道道的学者风度。高高的个子,慈眉善目,衣服干净挺括,一尘不染,名副其实的教授形象。”
写林先生的生活:下乡做社会调查时,看见窗纸发白,林先生脱口而出:“杨柳岸,晓风残月……”接着就站起来,“老吴,我们该出发了……”当肚子咕咕一响,林先生边吟诗:“且食勿踟蹰,南风吹作竹。”边信步走进路旁饭店。真是触境生诗,行随诗动,把诗和生活水乳交融在一起了。
当年作者喜欢林先生的诗集,在课堂上看,工宣队的迟师傅准备抓他现行,结果却被作者戏弄了一番。本是为林先生出了口气,但林先生却开导作者,要尊重人,特别要尊重那像迟师傅这样念书不多的人。
严家炎先生是吴宝三先生最亲密、最知心的师长。书中专写严家炎先生的文章就有三篇。
严先生的特点是“严”。无论做学问还是为人处事,一向严谨缜密、一丝不苟、严上加严。严先生写给作者的三十几封信,每一封的地址、邮票粘贴都一丝不苟;严先生被老伴儿称为“书虫”,唐弢先生称他“有点固执”,也正是这种认真,成就了他的学术造就和对人才培养的累累硕果:他和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全国高校中文系通用教材,并荣获全国首届优秀教材奖。
严先生做学问、处事严谨,对朋友亦十分重感情。严先生对作者亦有知遇之恩,不仅传道授业解惑,还是作者在大学的入党培养人。就是这种知遇之恩,奠定了作者和严先生俩人的半世情谊。作者参加工作后,虽然与严先生身处两地,但联系却没中断。作者进京必拜访恩师,严先生也数次到兴城和哈尔滨去看望作者,给孩子买玩具,给作者买胃药。作者到了北京,严先生亲自下厨做菜……这两位文化名人半生的交往和情感,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师生之谊。
马振方教授是吴宝三在北大上学结识的第一位老师。他幽默风趣,常和学生们打成一片。
作者的北大恩师高人林立、性情各异:唐诗研究大家、 心性真淳如大男孩的陈贻焮教授;鲁迅的忘年交、扫地僧般在北大中文系看门、摇铃、接电话的川岛(章廷谦)先生;大学刚毕业就合作主编《中国文学史》、“官升脾气不长”的费振刚教授;挑名作名刊毛病讲语言课、自然质朴的朱德熙先生;敢讲真话的小说家、带呢帽、叼烟斗的吴组缃先生;知识渊博的学界杂家吴小如先生;所著《新文学史稿》作为全国大学教材一版再版、笑声琅琅、目光炯炯的王瑶先生;语言文字大师、红光满面的王力教授……诸位大师在作者朴素的笔下形神毕肖,令人心向往之。
作者书中所涉的部分名人或文章,以前曾在语文教材上见到。读《在北大上学的日子》,方知是吴宝三先生的老师和同学,顿生亲近之感。比如袁行霈先生,高中语文教材的总主编,多年高冷地印在扉页上。看过书方知,他是林庚先生的得意弟子,这个多年高高在上的名字,一下子变成有血有肉、鲜活可爱的人走下纸来;读林庚先生的《说木叶》,求根溯源、旁征博引,耐心细致、自然有味儿。当年就想,能把“木叶”二字写出洋洋数千言、赏析得如此通透周详,该是个怎样的学者呢?不想,竟是我所尊敬的吴宝三先生的授业之师!忽感如此亲切,仿佛自己这株小草也落入了文化森林中;温儒敏等编的中文研究生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虽为学术著作,但语言朴素干净、文风亲切自然,仿佛能看到编者的净朗敦厚,原来亦与吴宝三先生师出同门。吴老这部著作,也同样让我感受到《说木叶》《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自然亲切。这种感受,或许就是北大中文深厚内力的自然散发,就像光之于火焰。
吴宝三先生这本书写到的人和事,我以为会载入北大研究史册,虽然是一本散文集,却有无可置疑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