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抵达时间尽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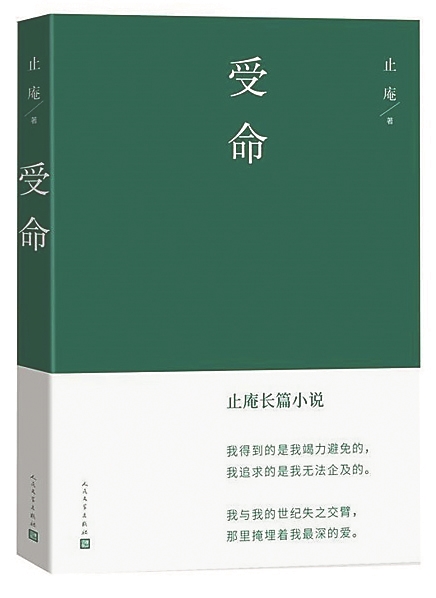
《受命》 止庵/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6月
□温玉晶
《受命》是止庵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据说他从1988年开始着手积累素材,历经三十余年才完成。背景是北京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风貌:街道、医院、电影院、副食商店、饭馆、公园,包括女孩子朴素或时髦的打扮及物价,事无巨细地贯穿在几个人物的生活中。我虽未曾亲眼见证彼时的景象,可通过小说也能在脑海中构建得七七八八,可见止庵的工作之细致,推敲之严谨。
小说的序章,描写了一名医生极其平凡平淡的一天,并且“不出意外日复一日可能要在同一岗位干到退休。”而正如“受命”这个强有力不允拒绝的标题一般,这个“意外”迅速地在第一章就劈进了主人公冰锋的生活。
关于复仇我们总有各种想象:手刃仇人的快意,同归于尽的悲壮,宽容慈悲的谅解,时过境迁的“算了”……可似乎哪一种都难以言尽个中滋味。对于冰锋而言,复仇的“受命”是层层递进的,母亲告知其父亲被迫害最后自尽的遭遇,他找到父亲破碎的“遗言”,给冰锋的心上劈开了一道口子,随即,贺叔叔的劝解像是在这道口子上试探:是要将其缝合,还是撕裂?而后母亲患上阿尔茨海默症,贺叔叔病故,这两个知情人,顺遂时间的巨浪而来,短暂地靠了靠岸,仿佛完成了使命一般,转瞬又被卷入,冲刷得干干净净。
“受命”的“命”是父之命,母之命,更是天之命。“历史不能总是一笔糊涂账,个人也要负责。”——他抱着这个执念把口子撕裂得更大,大到必须得往这个裂缝中钉下一根柱子,再用一根利刺将自己钉入这根柱子,才能立住,避免被裹挟。他坚信自己就是那个被指定的,能够清算这笔糊涂账的“受命者”。
对于冰锋而言,身怀复仇的使命便是这种“入魔”,但这种“魔”并非是“恶的魔”,它是带着真和善的“魔”,甚至是带着“义”的“魔”。“真”,是为父亲悲惨境遇追根溯源;“善”,是为历史的旧账除恶;“义”,是伍子胥式的日暮途穷下的自持,是明知是“魔”仍执意入“魔”的坚毅。
冰锋心中的“魔”驱使着他去打探仇人的线索,谋划行动的实施。而同时存于他心中的“美”又让他加入诗歌小组,认识了祝叶生。尽管他不愿将与祝叶生的感情牵扯进他的复仇计划,他要保证这个复仇是“干净的”,一对一的,不拉扯其他人的,可命运暗涌波动,在暗处早已交汇融合,难以剥离——这何尝不是另一个层面的“受命”?
“入魔界难”。何况冰锋身边还有一位“活在当下”的现实的“凡人”丁芸芸,和受父辈光芒笼罩的圣洁的“佛”祝叶生。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写道:我们的“自我”或自我认知可以用一只漏气的气球来作比方——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他人的爱(对于气球而言便是氦气)来填充,经不起针尖麦芒大的刺伤。冰锋正好相反,他的“受命”是这只气球,父亲的遭遇,母亲患病前的嘱托,贺叔叔的劝解,伍子胥的故事,无疑就是注入这只气球的氦气,而祝叶生和丁芸芸的爱,则是针尖麦芒,将其欲入魔的气球一点点刺破,不经意的,遍布的,以至冰锋察觉并多次试图修补——对叶生保持距离,克制男女激情,拒绝芸芸考研、同去深圳的提议,不惜以分手为代价——仍无济于事,把他钉在那根柱子上的利刺时刻扎醒他,在时间的潮流中,他选择被钉住,艰难地屹立着。他必须完成这个“义”,这个“入魔”,这个“受命”,这只破绽百出的气球,哪怕是草率地选择了行动时机,他也得坚定地揣着,去往临界点亲手将它压爆。
书中提到冰锋几次到父亲自杀前居住过的地下室,躺在父亲躺着死去的地方,猜测他最后看到的景象。类似的情节我在一部日剧中也看到过,身为警察的父亲死因成谜,女主人公也成为一名警察后,每每到事件现场,便躺到死者的位置,据说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死者,感受到死者的意念。前几次我也把此举理解成冰锋试图靠近父亲理解父亲的想法,读到中途,我想不妨把这个举动也理解成冰锋在填充“入魔”的气球。抚摸父亲的指甲痕迹,写关于伍子胥的诗剧,一切都是在对抗时间的前进,他拒绝“活在当下”——考研或与丁芸芸去深圳打拼,他也拒绝“走进明天”——与祝叶生结婚一同出国,他通过种种举动,来提醒自己的“受命”,一次次差点要走出历史,又逆返。
祝叶生和丁芸芸刚开始在冰锋眼中,应该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出身显赫,难解世间疾苦,天生就带着任性满满的底气;后者出身困苦,于是脚踏实地,通过将自己和“自己人”的生活安排得节奏规律,有条不紊来补足后天的底气;前者是高耸天空的粉色云团,自由随性,有股子韧性却也脆弱;后者是图纸上比着尺子画的横平竖直,气势磅礴且不容有误。她们都为了生活或是理想,大踏步往前去了,留下了冰锋,这个选择留在历史中,又拼命想与时间赛跑的人。
叶生前后言行的转变,可以肯定的是看了日记的。而冰锋复仇那晚做了什么?伍子胥的诗剧他会不会写完?即使是最终章铁峰所叙述的过程,可能也隐去了一些细节,我们无从得知。小说末尾的临空失脚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但你就是能感受到,它堵塞在你的心脏与唇齿之间的部位,想吸收却无能为力,想吐露却也终不得法。
止庵老师在这部小说中,展露了他深藏的才情,一改以往置身事外隔岸观火般的评论式文字,处处透着他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生活的“置身其中”,尤其爱报菜名,引人垂涎,通过文字能感受到他的隐忍、舒展或是爆发。
在时间面前,冰锋没有跑赢,仇人也没有跑赢,他们同归于尽于时间中,这也许是复仇最好的结局。可《受命》不宥于时间空间,那些留白的想象的多义性,如此迷人,值得一读再读,无穷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