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慢及其美学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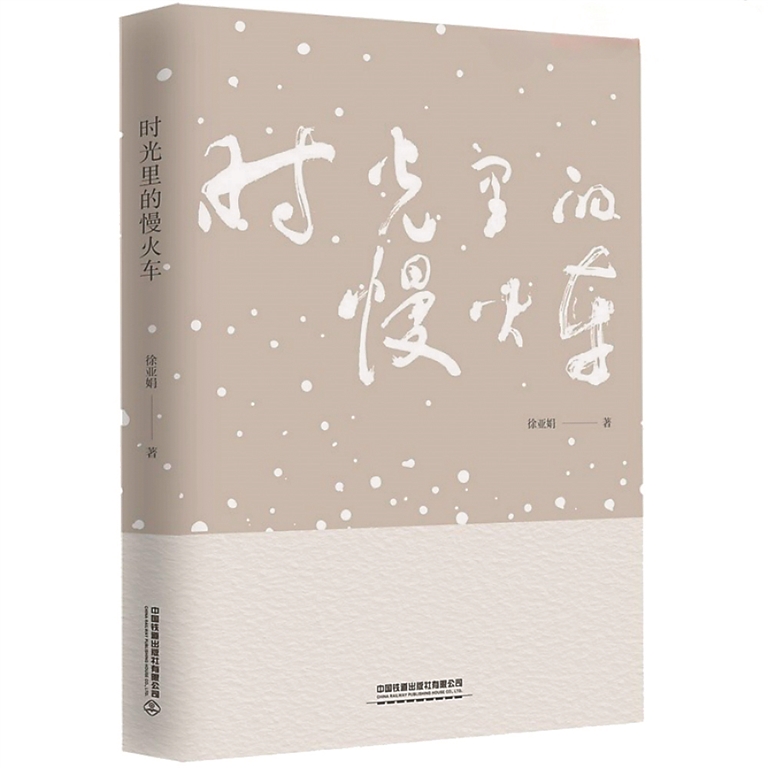
□姜超
1810年,斯蒂芬森开始制造蒸汽机车。1814年,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名唤“旅行者号”的蒸汽机车。机车行进时燃烧之火从烟囱冒出来,“火车”自兹而来。在我国,火车这个称谓长期是文明的象征,嵌入在更加悠久的农业文明的整体氛围中,化为独特诗意之一种。
火车,本是工业化的产物,但在徐亚娟笔下缱绻为诗,化作后工业时代的一种乡愁。带有缓慢气质的绿皮车,行进在前现代的城乡之间,与记忆的天然属性高度类似。幼时的远处观望、少年时求学的乘车故事,经记忆坩埚的重新熔炼,忽然有了闪光的欲望,这些倾诉驱使文字诉说,写作者似乎就可以走笔成章了。及至作家本人成为铁路职工,关于铁路的轶事多了深情凝望的亲切感,穿越时代的小叙事漫漶不绝,遂成一部散文集《时光里的慢火车》。
闲身跳出红尘外,徐亚娟打磨的散文,激荡着远行人的浪漫情怀,多少覆盖着守成守旧主义的倾向。那些说走就走的旅行足以快慰平生,率性而为的文字带着小意绪、小情调甚至有点小可爱,像一帧帧生活的速写。徐亚娟与大多数人一样有着浓郁的“城愁”——在都市中晕头转向,在喧嚣里无所适从。好在她并不去效仿抒情诗人的做派,径直行走天地之间,而是选择自己最熟稔的“火车”作为“取景器”,观世界之“侨易”,而取内心安稳之“象”。
散文家提笔之前,他肯定有明确的表达方向。“为天地立心”过于宏大,如徐亚娟“为自己立心”的散文之路则更接近写作的本源。《时光里的慢火车》从个人成长出发,当然也是作者的心灵史。很多作家在描述自身从事的行业时,或批判其弊端,或者单纯讴歌行业属性,入骨入肉的描写较为少见。至少在徐亚娟笔下,铁路不是单纯之物,她赋予其更多的人文价值——让冰凉冷硬的“铁路”与声噪四方的“火车”附着了温情,成为人间喜怒哀愁的置放处。作为高度人格化的物象,铁路、火车贴近了写作者与读者。因为这样的随性,徐亚娟的散文亲如家常,也有感心动耳的感染力。
还得郑重提及散文集名称的“慢”字,全书之魂赖于此也。散文《行走在兴安岭上的慢火车》走笔从容:“小镇上的炊烟在火车行进间袅袅升起,晨昏日暮,这列火车是乡邻们生命的托付与佑护。四季风光旖旎变换,不论山花烂漫还是秋色浸染,不论是老树发芽还是大雪封山,这列火车古朴的绿色车体都会在山林间蜿蜒穿行,钢铁之躯与草木鸟兽友伴同行互不惊扰。几十年如一日,这列火车带着原始没有雕琢的诚意如期而至,数十年不变的票价,数十年不变的行程。”
慢能引导人收声敛气、沉思静观。缓慢,最接近神思回转,迫人陷入回忆之境。我以为,徐亚娟的这些篇章似在作反向努力——回归童年,返抵故乡。如老子云:“反者,道之动”,他强调“复归于朴”的珍贵——人首先要找回质朴的内心;其次要回归朴素的语言,避免语言暴力、伪饰过度。一言以蔽之,徐亚娟竭力在回归朴素,这是人生最大的凯旋。
作者虽未言明,我们很容易判断徐亚娟的精神旨向。世界越来越向物质偏斜,鲁迅早年批判的“文化偏至(即朝向物质、技术、机器等方面)”在现世大行其道。徐亚娟的散文书写像青草一样生长,奋力洄游,对文化传统予以精心守护。浪漫不是作家的自认,而是读者阅读时贪图省事顺手给的主观评价。《火车承载的时光》一文有一段夫子自道的剖白——“火车是我相敬如宾的老朋友,我们彼此善待,聚散随缘。火车是我休戚与共的兄弟,我们彼此守望,不离不弃。我生活的城市,那里是我旅途的起点,火车一直等在那里,等我出发,等我遇见,等我平安到达。”隐而不彰的散文气韵间,徐亚娟保持难得的书香襟怀、山川心胸,她还葆有真正的热忱、纯粹的追求。
久思远想固然可敬,若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乱了心智,则不如徐亚娟一样专心当下、专注手头的事情,对当下生活予以细致深情的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