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大学和学科能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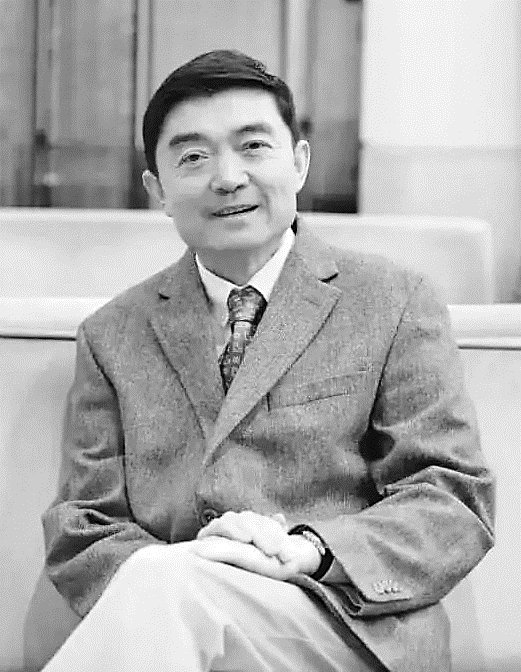
陈松蹊

姜亚军

汤建民
“加快‘双一流’建设”,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里的这7个字,字少事大。
实际上,早在4个月前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的联组会议上,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就表示,将聚焦优势学科适度扩大“双一流”建设范围。
中国此前已有过两轮“双一流”建设。
2017年,全国140所高校与465个学科入选第一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5年后,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围绕基础学科等国家急需领域,“双一流”的名单里又新增7所高校、41个学科。
现在,新一轮的“双一流”扩容已然启动。
今年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西南科技大学副校长尚丽平在《关于“双一流”扩容增设区域急需赛道的建议》中提到,当前“双一流”建设高校呈现“东部多、中西部少”“省会城市多、非省会城市少”的特点。目前,中国“双一流”建设高校仅147所,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中仅占5.13%,与充分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要求还存在差距,推进“双一流”扩容成为大势所趋。
就本轮“双一流”扩容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系教授陈松蹊,全国政协委员、西安外国语大学原副校长姜亚军,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中国科教评价研究院副院长汤建民日前进行了深入探讨。
区域不平衡不易达成共识
在本轮“双一流”扩容中,可以优先扩容哪些学科方向?
陈松蹊:我觉得应该优先扩容国家急需的学科,以及此前“双一流”布局覆盖不足的学科。比如作为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基础的统计学的布局就不足。在第一轮和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中,统计学入选“双一流”学科建设的高校总共不到10个。
想要发展人工智能,计算机、统计学和数学都是基础。但大家对统计学的认识往往不足,要不认为它是数学,要不就认为它是社会科学。美国人工智能做得比较好,高校的统计系很多,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有力基础。
除了国家比较急需的学科,在空间上,我认为应该向目前“双一流”高校数量少或没有“双一流”高校的省市倾斜,同时在社会科学领域也应该有所布局。“卡脖子”问题也就是这几年的事,眼光可以放得更长远——如果“双一流”建设学科都集中在某些学科,可能会在今后出现过剩。
此轮“双一流”扩容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自主科学确定“双一流”标准。与前两轮相比,第三轮“双一流”评选可以有哪些调整?
汤建民:作为多年从事大学及学科专业评价研究的学者,我认为,与前两轮相比,第三轮“双一流”评选在指导思想和评选标准上,可以由原来的侧重“实力评价”,进一步扩展为“实力评价”“增值评价”“未来适应性评价”的模式,以更好地适应时代的需要。
“实力评价”考察的是现在的状况,“增值评价”考察的是过去一轮或二轮周期内的进步或退步程度,“未来适应性评价”考察的是适应未来10到20年时代变化的可能性,以保证“双一流”的学科设置能更好地适应未来时代需求。
有一种声音是,东部地区高校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如果用“一把尺子”衡量不同地区的所有高校,会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高等教育水平的差距。因此应该考虑人口因素和区域布局的平衡性,重点在人口大省和“双一流”布局较少的地区扩大“双一流”建设范围,怎样看这种观点。
姜亚军:“双一流”扩容需要考虑区域均衡问题,这关系到教育的公平性。尽管当年国家做了很多布局,但中西部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在教育理念、师资队伍等方面,多年来也产生了很多问题。
汤建民:不平衡是一种普遍现象,也是一个不易达成共识的问题。目前的“双一流”布局中确实存在不平衡的问题。但我仍然不太赞成将地域、人口等因素简单地或者说过紧地与“双一流”设置捆绑在一起。“双一流”建设主要是国家层面的布局,主要判断标准是,看能不能更快地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当然,公平性问题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应该在具体操作上更多地考虑进去。我认为,可以将扩容的学科简单地分为 “前沿突破型”“行业支撑型”和“文化传承型”三大类。
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为了抢抓机遇,我们的扩容重点更多地可能要安排在“前沿突破型”这一类别上。对“前沿突破型”的遴选,主要是要看其学科的目前水平和未来适应性,而不宜掺杂其他非学术类因素。而对于常规的“行业支撑型”和“文化传承型”学科,则可以更多地综合考虑地域、人口等因素。
公平性的另一面是科学性,在考虑区域布局公平性的同时,是否会影响到评选的科学性,降低“双一流”入围质量?
姜亚军:这个倒不好说。前两轮“双一流”建设,不管高等教育整体水平怎么样,原来没有985院校的几个省份,最后都有学校入选“双一流”名单。这些学校的平台会更高,在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引进等方面都会更有优势,对人才的挽留也会起到很大作用。比如河南是人口和高考大省,让两所“双一流”高校快速成长,对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不可估量。
应明确“下车”的标准
教育部曾明确“双一流”建设“不搞终身制”,承诺进行动态调整。但目前仍没有高校“下车”,此前被公开警示的学科也保级成功。做减量难在哪里?
汤建民:“双一流”的评选标准包含多个维度,是综合评价的结果,而不是由单纯的定量计算得出来的,因此入选标准本身存在一定模糊性。如果现在要求某校某学科“下车”,要拿出一个过硬的理由是比较困难的。
目前的大背景仍是扩容,在这种大背景下,要求做减法就更困难。而且要求某校某学科“下车”,可能会对相关单位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双一流”建设如何才能实现动态调整?
姜亚军:第一轮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中,分为A、B两类。其中把有些发展比较慢的学校列入了B类,这也是对他们的一种警示。
汤建民:做减量尽管是有必要的,但我认为,这个设想的实现也许需要更长的时间。后续比较可行的方法,首先是要继续进行监测评价,对建设成效不佳的继续予以公开警示,如果以后连续2轮或3轮仍受到公开警示的,则可以让其“下车”。同时也可以考虑新构建一个明确的关于“下车”的评价标准体系,凡是符合“下车”标准的则让其“下车”,以打破目前比较僵化的局面。
优质本科扩招非常复杂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扎实推进优质本科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介绍,进一步增加“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的规模。在2024年扩招1.6万人基础上,2025年力争再增加2万人。怎么看?
姜亚军:我们教育界别有不少大学书记校长,小组讨论时大家谈得也比较多,都在关心这事。优质本科扩招基于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也能让更多的学生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那些书记校长们说,国家要求扩招我们义不容辞。但优质本科扩招,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书记校长们觉得政府工作报告说得对,但建议在前面加半句话,“加强投入”。到目前为止,应该怎样投入,还没有明确。
现在不少省份也在启动地方的“双一流”建设,甚至今年有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将职业本科纳入“双一流”建设评价体系。“双一流”是高校应该普遍追求的办学目标吗?
汤建民:职业本科院校还是不宜纳入“双一流”建设评价体系。职业本科院校可以继续在“双高”建设行列中发展。
“双一流”不必要也不可能是各高校普遍追求的办学目标。中国地域辽阔,发展也不平衡,各校的发展历史、发展定位、发展状况也多种多样。各高校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确定合适的发展目标,而不是统一将“双一流”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
姜亚军:“双一流”是一个名号。刚才我们也讲到分类发展,地方院校应该把自己定位在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上面。比如新疆的学校,可以发展服务于同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经贸往来和区域经济的专业。
杜寒三